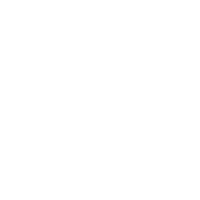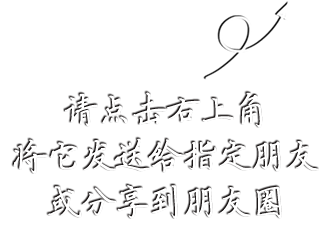童年的一次遇险经历
邱昭山
上小学一年级前,我掉进老家的水井里一次,是母亲和邻居单大爷救了我。
我的故乡是五龙河畔的柴沟村。我们家的祖居是离五龙河不远的两进院落,连带一条小胡同。前面一趟是五间高大的、当年看起来确有些气派、建于清末的房屋,山墙用青砖垒成,腰线以下也是青砖,前后出厦(屋檐用短木板挑出去一截),白石灰掺着细细的麦糠抹就的坚实外墙皮。后面一趟是六间矮一些、建筑质量差一些的房屋,最西头的一间是过堂,过堂向南通着小胡同,过堂和小胡同供住在两进院落的人出入。听祖母讲,我曾祖父很会过日子,攒下了一份不薄的家业,开着赁铺和油坊,有地几十亩,有东西南北相连的四进房子。日本鬼子打进高密的时候分家,我大爷爷分到了赁铺和东边两进院落,我爷爷分到了油坊和西边两进院落。我爷爷(外号“二少”)不谙农事,又好抽大烟,好结交朋友,等“八路”来的时候,分到的家底基本被他挥霍掉了,地没有了,油坊垮了,只剩下了两进院落。祖母说,也亏他能“祸跳”,划成分的时候,我们家才被划成了中农。全国解放后,一公家单位看中了我们家临东西大街的那趟房屋,想租用,找村干部来说事,没有文化、但历经风雨的祖母知道轻重,他对村干部说:“让他们情管住,俺一分钱也不要。他们自要住一天,俺不能说(这屋)是俺的。”这家单位搬走后,柴沟公社药材组又搬进去住。
大概在1974年,药材组从我们家临街的老屋搬走,搬到村后的另一条东西大街上去了。祖母找了两个有威望的邻亲当分居人,给我父母和二叔二婶母分了家。经母亲和二婶母抓阄,我父母分到了药材组原来住的那趟房屋,二叔二婶母分到了前面的那趟房屋。前后两进院子里和小胡同的一侧植有几十棵高大的榆树。药材组搬走后,父亲瞅空到后面那进院子里去,爬上榆树,用镰刀穿了穿树枝子,带着毛茸茸的紫色花苞的榆树枝子落了一地。我清楚地记得,那时,靠南屋墙根儿的树底下,堆放着一些破砖乱瓦,一些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小甜瓜状、表面分瓣、已经锈蚀了的手雷。
星期日这天,在生产队里当保管的父亲看管场院去了。按照父亲的安排,母亲带着哥哥、我和哥哥的一个同学都到后面院子里拖榆树枝子,拖到东西两边的院墙根儿,垛起来,以便晒干了做烧草。时值初春,院子里几畦子菜地种的韭菜已从土里探出了黄灿灿、脆生生的可爱脑袋。我边拖着树枝子,边倒退着走。看到哥哥和他的那个同学走进了韭菜地,好管闲事的我大喊起来:“别踩着韭菜!别踩着……”未等我喊完,“咕咚”一声,一下子掉到了水井里。
院子里靠西的这口水井,有七八米深,井壁光滑,立陡,长满了青苔,也不知是哪年挖的。平时,这井台上原来有辘轳,药材组的人从井里打上水来,浇浇菜,洗洗刷刷,但因为是“懒水”,他们不会烧开了当饮用水喝,我们家或者住斜对门的单大爷等邻居要用水洗洗冲冲的,也常到这井里打水。我掉到井里的时候,可能是因为药材组搬家搬的,那辘轳不知弄到哪里去了,只剩下了一个光秃秃的井筒子。
穿着棉袄的我从井底浮了起来。这时,井上面的人忙活起来。母亲迅速找来了水筲,绑上绳子,往井里续。这时,我看到的井口还不如一只碗口大,井口上的几个人影像蚂蚁那样小。水筲挨着水面了,母亲大张着口,好像在大声喊我。我两耳浸了水,听不到喊声,但我意识到母亲是叫我抓着绳子或者水筲的边缘,她好把我连同水筲一起提上去。可能是母亲太紧张了,绳子和水筲一个劲儿地抖动,我好不容易抓住了,母亲往上提,我一失手,“咕咚”一声,又掉到水里了。可能因为我穿着棉袄,加之又是个孩子,在水里浮力较大,所以我接着浮了上来。
一旦我的棉袄浸透了水,我再沉到水底,就很难救了。时间就是生命!母亲来不及到生产队里的场院找父亲,她急匆匆过了街,去斜对门找会剃头的单大爷。在母亲去找单大爷的时候,我感到井水凉凉的,浸润着脖子、脊梁,而且正一个劲儿地往棉袄、棉裤里钻。我第一次感觉到:“我会死吗?我要是淹死了,娘会多难受啊。”我哭了起来。
似乎过了很长时间(其实只是一小会儿),我看到井口出现了会剃头的、黑脸的单大爷的身影。他看到我仰躺在水面上,一边叫着我的小名,叫我不要哭,也不要动(这是我后来听说的),一边把绑着绳子的水筲续到井里,让我抓住绳子或水筲的边沿,但我还是抓不住。已经过了一会儿,我还是静静地仰躺着,我觉得自己真的完了,不由得一个劲儿地流眼泪。
还是单大爷有经验,他可能觉着趴在井台上捞人,不好把控软乎乎的绳子,就下到井筒里,在井口上露出上半身,下面两只脚分开,用力踩住井壁上原来凿出的、方便打井人上下的跐洞,再低头用绳子把水筲从两腿中间续下来。他踩井壁的时候,有壁土掉了下来,迷了我的一只眼。等水筲续到了仰躺着的我面前,我竭力睁开另一只没被壁土迷了的眼,举起两手,试了几次,终于用一只手够着了水筲的边沿,用另一只手抓着了水筲的巴梁。单大爷看到我抓住了,小心地、慢慢地、像蜗牛爬动一样地向上提绳子,终于把水筲和我提出了井筒。一直站在一旁的母亲一把抱住我,抱到井沿上,就坐下去了,眼泪也“刷”地涌了下来。
第二日,母亲按照风俗,在一只长柄的炒勺里加上豆油,放上一块黄黄的鱼鳔,在炒勺下烧火,把鱼漂炸了,给我吃,说是防惊吓。那鱼漂香喷喷的,不懂事的我吃完,喊道:“真好吃!”母亲还到井沿边烧了纸,感谢神灵的保佑。当时,我感觉自己在井水里躺了好几个钟头。听哥哥说,我实际在井里呆了接近二十分钟;在从井里捞我的过程中,母亲的脸赤红赤红的,浑身直抖,汗水“披沥披沥”地淌。后来,母亲不幸亡故,父亲在院子里靠东的位置打了一口小型的水压井,把我掉进过一回的那口水井填平了。
几十年来,故乡经过多次改造,容貌大变,我生活过的老屋、院子,以及那口让我惊心动魄的老井,都早已不见了踪影。但有时回到故乡,我似乎还能嗅到一些气息——老宅院的气息,母亲的气息……